想找出答案,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英]迈克尔·布拉斯兰德 张濛 译
定理或任何其他抽象的准则或原理永远承受着一份压力,那就是如何与许多真实事例联系起来,既不能太过模糊或抽象,以至于派不上用场,又不能受特定场景下限制条件的约束,以至于失去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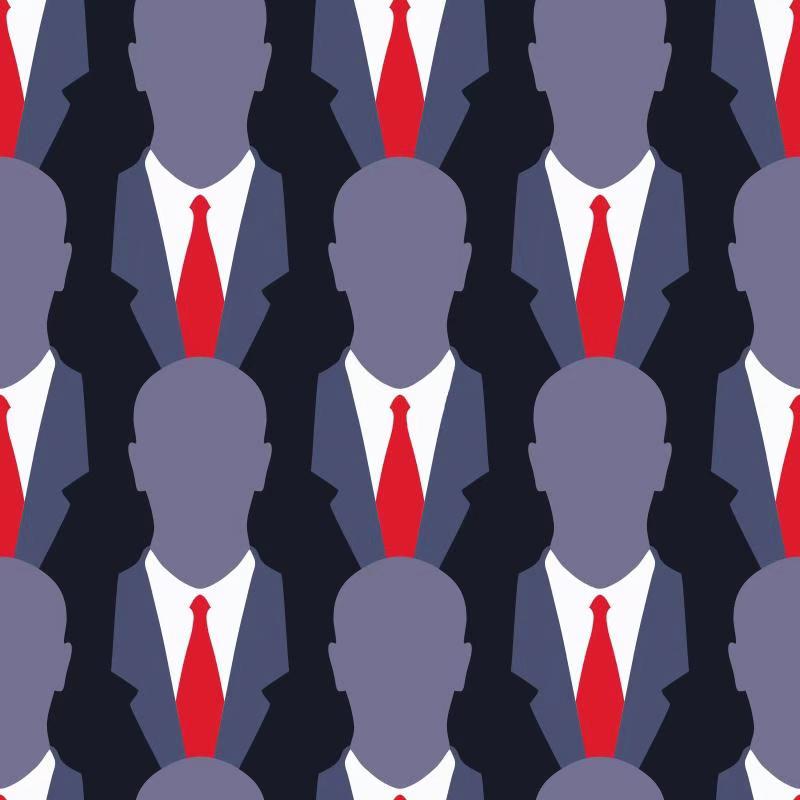
1984年,罗伯特·西奥迪尼写了一本书,名叫《影响:说服的心理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人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我们倾向于随大溜,尤其是当自己拿不准的时候,我们会从他人那里寻求线索,以做出正确或最佳的决定。西奥迪尼称之为“影响力武器”。书中记述了一项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实验:假如有些人故意仰望天空,那么路人也都会这么做。也许我们并不需要一条定理来告诉我们这一点,但的确存在这样一条定理,它被称为“社会认同理论”。西奥迪尼将那一章命名为“我们即真理”。
事实的确如此。社会认同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西奥迪尼说,为电视喜剧节目提前录制的笑声,就是这个道理。当听见其他人笑时,你也会跟着笑(制片人就是这么希望的)。
最近就发生了一个试图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实例——英国的政府顾问们试图利用社会认同理论,说服更多人登记器官捐献。任何一根充满希望的理论稻草,政府都会将其握在手中,假如它正好与其他政治目的相契合,那就更是如此了。明智的是,行为洞察团队——也被称为“助推小组”——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进行了一项实验,测试了蕴含这条理论的信息对他人的影响。
器官捐献运动的目标群体,是上政府网站更新驾照的人。助推小组选择了3条包含社会认同理论的信息。他们给一些人展示其中的一条,大意是:“许多人都同意在死后捐献器官,也许你也想这么做。”而对其他人,他们则分别展示了不同的信息,如大意是:“请同意捐献。”或者:“有一天你也可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为什么不帮帮别人呢?”这项实验持续了5周,每条信息都有10多万人浏览。
结果全部3条包含社会认同理论的信息都不如最佳替换方案有效。这个替换方案就是基于最简单的互惠原理:“如果你需要接受器官捐赠,你会得到所需器官吗?如果会,请帮助他人。”在3条包含社会认同的信息中,有一条还附上了图片(在过往的实验中,附上图片通常能增加访问者的回应),结果这条信息是他们尝试的全部8种展示方式中最不成功的一种。
作家兼播音员蒂姆·哈福德令我注意到了这个例子。蒂姆对行为经济学有一定的了解,对该领域十分感兴趣。他称社会认同理论时而有效、时而无效的现象是“令人不安的”,并写道:“社会认同在心理学上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正如器官捐献实验的结果所示,它并非总能适用,而且难以预测它何时适用、为何适用。这些时而无效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虽不至于撼动整个领域的权威性,却增加了制定切实可行政策的复杂性。”
我们如何知道是否该运用这一理论?它究竟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些不确定性肯定了行为洞察团队所采取的实验方法的价值。他们先是选定一条定理,将其设计成一项实验,再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它在某个特定情境中有效,那么很好,定理奏效;反之,则停止实验。正如这个团队在回顾整个器官捐献实验时所说的那样,实验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注册器官捐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验证行为科学理论的效用,以提高其他领域的政策水平。”
虽然并非所有理论都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但如果可以,在有限情境下进行的定理实验,是可以有力地表明:要么该定理在此时此地有效,要么它无法普适。这样做要么扩展了该定理的有效范围,要么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无论怎样,我们都会有所收获。但我们必须找出这个答案,而这个过程一定是极为务实的,容不得任何前提假设。
蒂姆·哈福德表示,难点在于,我们既要完善某一定理,同时“又要不使其陷入一堆特殊事例的泥潭”。这令我想起了所有理论都必须面对的那个终极挑战——既要保持普适性,又要细化,以应对更多的细节问题。我们必然失去一样:要么是理论的一致性,要么是它在具体事例中的效力。行为经济学的泰斗之一——理查德·泰勒曾说:“假如你想要一个统一的经济行为理论,那么新古典主义模型就是不二选择,但它并不能很好地描述现实决策的制定过程。”
这是一种不幸但又无法避免的权衡:拥有统一性往往就会失去实践性;或者拥有独特性,也许对部分有帮助,但又会出现碎片化或混乱的情况。在一个丁卯分明的世界里,这两方面不会存在矛盾;但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两方面各自的局限性。
蒂姆·哈福德指出,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知道某个理论在下一个事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简而言之,我们不知道。我们决定是否运用某个理论,几乎就如同在下赌注,充其量是掌握了一点理论知识的赌注。下赌注的关键点在于,要记住我们是在打赌,我们可能一无所获。并非因为赌注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就是在践行严谨的科学。
在我们认为理论与实际问题不相关并忽略它之前,还有一个难题:我们往往别无选择,而不得不依靠它。如果我们对引发现象的潜在机制缺乏一定的认识,那我们就更不能确定理论是否能普适了。理论就是我们试图识别那些机制并解释它们是如何共同作用以产生诱因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婴儿死亡率或犯罪率会降低,那我们如何指望在其他地方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或是维持这种情况呢?即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班纳吉的地方实用主义,也在寻找一套机制,无论这套机制多么微妙复杂。
事实上,如果在研究某个问题时缺少相应的理论告诉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如何积累证据,以及为何该理论能够解答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甚至根本无法开展研究工作。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探究行为本身就是由理论所塑造的。即使我们完全拒绝一般性的理论,到最后,取而代之的仍会是大量的小范围适用的局部理论。在这一观点上,人们并未全然否定抽象准则,他们只是担心这些准则是否能应对各不相同的、日常的偶发事件。
这里有两个术语: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内部效度是指我们认为在原始的研究情境和条件下,我们的知识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外部效度则泛指这一知识可以普适于其他情境之中。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概念,区分了在某种情境中有效的观点和推广到其他情境中依然有效的观点。在抽象准则的框架内也存在这样一个术语,被称为“分析效度”。当某个抽象的准则可以适用于现实问题时,它就是具有分析效度的。事实证明,这个目标既必要又难以实现。我们试图找出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运行机制,但它们都将各自的秘密隐藏得很好,而且往往都藏在大量的神秘细节之中。所以,理论及其他一般原理常常是不可靠的。它们相互矛盾,不稳定,缺少预测能力,根本不切实际,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随它们。
这些困难表明,想找出答案,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用埃斯特·迪弗洛的话说,就是必须去干干当地水管工的工作——这往往是最理想的状态。其言外之意是,在数据、实地的实践实验(可能的话)、即兴的假设、对方法的反思之间,应该存在一场永恒的对话,我们应该通过实验和犯错来不断重新审视这些。而且尽管我们极其努力,依然会失败。总之,我们不是说社会学家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非常优秀——只是说,想得到可行的社会学理论,与要运用该理论所研究的难题一样难。千头万绪的生活,绝不会让我们轻易看清它的面貌,我们应当拭目以待。
(摘自《暗知识:你的认知正在阻碍你》一书)
定理
理论
实践
发现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和纠错,及文章配图版权问题均请联系本网,我们将核实后即时删除。


